雪禅 水月楼 黑黑黑黑历史(2)
他是从不接客的,不过就是他接客应该也没什么客人会点——且不谈他那张桀骜到杀气腾腾的脸,正常人对一个有八块腹肌的小倌儿应该都不会产生什么性致。
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大马金刀的姿势坐在一张黄花梨木椅上,自顾自地喝酒。他喝酒向来不用酒盅,拿起酒壶仰头便灌。琥珀色的酒液淅淅沥沥洒下,有的落入两张薄唇间,有的洒在脸上,顺着他修长的脖颈流淌,流过突兀的喉结,最后缓缓渗进衣领里。
有些淫糜的画面,令人不由一时忽略他的桀骜冷厉,遐想着剥开那层微微润湿的衣料,一窥领口下的锁骨,饱满的胸膛,以及想必手感很好的皮肤。
如果忽略那煞风景的大马金刀坐姿,以及他背后的剑。
对,一口剑,暗金色的剑。没人见过他拔剑,甚至没人见过他把剑从背后取下。有人曾说那把剑其实被锁住了根本拔不出来——不过也只是传言而已,毕竟没有谁用自己的脑袋去试过。
所以比起那个奇奇怪怪的信佛的养子,这个小倌儿更加奇怪到了极点。
有人说那是老板豢养的宠,不过老板的口味也忒别致了点就是。
还有人说这人其实是个作恶多端的剑客,被老板囚禁于此偿还罪愆来。而老板也不是什么普通人,是个得道高僧。
这话是蝴蝶君说的,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曾来此男扮女装卖了段时间的艺,攒够了老婆本他就走了。在这儿卖艺的时候他还和人邪打过一架。鉴于他和人邪的私人恩怨,他的说法并不可靠。况且得道高僧是青楼老板这种荒谬的说法只有傻子才信。
每日大致便是如此,秋波盈盈的姑娘红袖招摇地揽客,台上的舞姬水袖甩出层层叠叠的花样——有时那舞姬是腰肢柔软的的男子,不过都是化了浓艳勾魂的妆,谁在意性别呢。老鸨如同每一个青楼里必有的笑容满面的老鸨招待常客。而那位特立独行的人邪就倚在他专属的黄花梨木椅上,喝他永远喝不完的酒。
信佛的养子每天都要听老鸨报前天的账——他有没有听就没人知道了,反正听之前和听之后都一样漠无表情。有时候手下人藏私虚报点数目他也不曾发现。管他呢,这么大的生意,谁在意这一点小损失。
听完(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听)报账他就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容去往二楼,那里安放着黄花梨木椅,他固定坐在黄花梨木椅边一张金丝楠木椅子上,手脚伶俐的小厮为这位少当家的奉上上好的香茗。这两位青楼奇葩就坐在一起,各饮各的。
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大马金刀的姿势坐在一张黄花梨木椅上,自顾自地喝酒。他喝酒向来不用酒盅,拿起酒壶仰头便灌。琥珀色的酒液淅淅沥沥洒下,有的落入两张薄唇间,有的洒在脸上,顺着他修长的脖颈流淌,流过突兀的喉结,最后缓缓渗进衣领里。
有些淫糜的画面,令人不由一时忽略他的桀骜冷厉,遐想着剥开那层微微润湿的衣料,一窥领口下的锁骨,饱满的胸膛,以及想必手感很好的皮肤。
如果忽略那煞风景的大马金刀坐姿,以及他背后的剑。
对,一口剑,暗金色的剑。没人见过他拔剑,甚至没人见过他把剑从背后取下。有人曾说那把剑其实被锁住了根本拔不出来——不过也只是传言而已,毕竟没有谁用自己的脑袋去试过。
所以比起那个奇奇怪怪的信佛的养子,这个小倌儿更加奇怪到了极点。
有人说那是老板豢养的宠,不过老板的口味也忒别致了点就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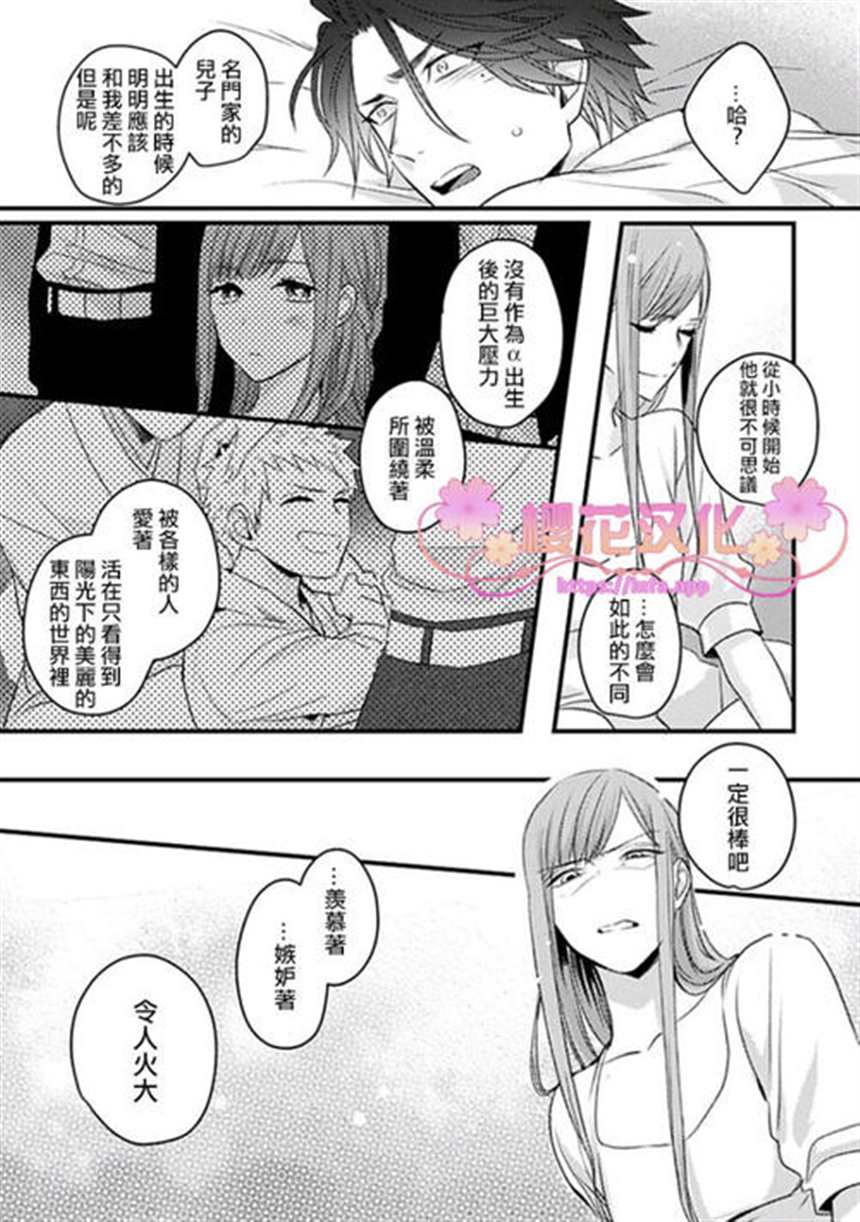
还有人说这人其实是个作恶多端的剑客,被老板囚禁于此偿还罪愆来。而老板也不是什么普通人,是个得道高僧。
这话是蝴蝶君说的,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曾来此男扮女装卖了段时间的艺,攒够了老婆本他就走了。在这儿卖艺的时候他还和人邪打过一架。鉴于他和人邪的私人恩怨,他的说法并不可靠。况且得道高僧是青楼老板这种荒谬的说法只有傻子才信。
每日大致便是如此,秋波盈盈的姑娘红袖招摇地揽客,台上的舞姬水袖甩出层层叠叠的花样——有时那舞姬是腰肢柔软的的男子,不过都是化了浓艳勾魂的妆,谁在意性别呢。老鸨如同每一个青楼里必有的笑容满面的老鸨招待常客。而那位特立独行的人邪就倚在他专属的黄花梨木椅上,喝他永远喝不完的酒。
信佛的养子每天都要听老鸨报前天的账——他有没有听就没人知道了,反正听之前和听之后都一样漠无表情。有时候手下人藏私虚报点数目他也不曾发现。管他呢,这么大的生意,谁在意这一点小损失。
听完(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听)报账他就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容去往二楼,那里安放着黄花梨木椅,他固定坐在黄花梨木椅边一张金丝楠木椅子上,手脚伶俐的小厮为这位少当家的奉上上好的香茗。这两位青楼奇葩就坐在一起,各饮各的。

 黑道上的名言
黑道上的名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